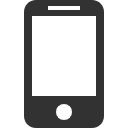酷阿鲸森林农场,正在慢慢“长大”。
不是突然有谁来改变它,也不是建起什么标志性的大建筑,而是每天都多出来一点东西:一块种出来的新菜地、一只跑进来的鸽子、一声不属于老成员的鸟鸣。
最早发现变化的是小白。
它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,绕着农场巡视一圈。灰兔跟着它走南坡,鼬獾则钻进木堆后面,从地下“通道”观察鸡窝和仓库。三者默契十足,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方式守着这一小片土地。
水渠边的浮萍越来越密,小鲸鱼顺着新修的水道经常游进来打个转,还会在某个午后跃出水面,把岸边晒的玉米溅湿一半。
黑鱼、河虾、鸡、鸭、青菜、葡萄、菌菇、蜂箱——每一样都开始有了规律的生长,每一样也都开始占据空间。地面上晒的是薄荷、干柚皮和蘑菇丝;草棚里挂着刚风干的鱼;厨房边放着一筐筐没来得及清洗的鸡蛋,甚至连鼬獾的巢穴边,都堆起了一叠备用木柴。
最直接的问题浮现了:住的地方,不够了。
原来的小屋只是当初的临时搭建,只有一间卧室、一张长桌和一个火炉,工具、食材、记录本、地图、草药、蘑菇干……全混在一起,连落脚的空位都显得拥挤。
卜丢看着墙角不断积累的纸箱、工具和盆栽,终于放下笔,挽起袖子。
“该盖房了。”
这次,他不打算将就。他在院子中央铺开手绘草图,用煤笔描出轮廓:
两栋三层木结构房屋,中间以通道相连。
一栋用作生活居住,有起居室、书房和卧室;
另一栋做为储物、晒场、工作坊和未来的“小型课堂”。
顶楼设露台种植区,墙角留鸟窝架,门前有可折叠棚架,阴雨可避、晴日可晒。
通道下留通风口与动物通行走道,小白、灰兔和鼬獾都能随意穿梭。
那天傍晚,小白躺在草图边看着他画图,偶尔抬头“哼”一声,仿佛在审阅。灰兔跳上砖堆,在未来的“阳台”上打个滚。鼬獾叼来一根竹子,试图插在地上,表示“参与”。
农场的框架,就这样在他们脚下铺开。
但还差一样东西。
一辆车。
之前的三轮电动车已经撑不住现在的规模了——进货要靠它、送鸡蛋靠它、去镇上换刀片也靠它。卜丢已经好几次在途中推车回家,电量不足、马力不够、装多了还会塌一边。
“得买辆皮卡。”他对小白说,“最好二手的,不怕划,不怕烂,不怕雨天泥地。”
他们在旧货市场上找了几天,也托村里留意。
第三天下午,一位从山城回来的木匠开着一辆蓝色旧皮卡来访。
“听说你们这地方,要盖正经的房了?”木匠笑着说,“我这车跑了十年,老是老,但稳。拉木头从不叫苦。”
他绕着农场转了一圈,最后说:“你给我三年的蜂蜜,我把车留这儿。”
交易达成。
车开进了农场的时候,小鲸鱼在水渠中跳了一下,水花正好落在车尾。
那天晚上,第一块地基打好,石灰冒着烟,锄头歇在门边,白色的车停在仓库下,像是早就属于这里。
灰兔钻进新打的基脚,鼬獾跳上未封顶的阳台,小白卧在门槛边,一只耳朵耷着,一只耳朵竖起,望着夜色里的远山。
卜丢合上图纸,轻声说:
“这儿终于要变成真正的‘家’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