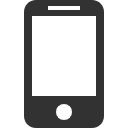房子真的开始动工了。
锯木、抬料、打桩、搭架,每天的节奏都像一首没有停顿的劳动诗。小白负责盯工地、守水管,灰兔早出晚归负责“巡视草地安全”,鼬獾则彻底接手了仓库区的“巡视与偷食”。
卜丢和几位木匠朋友则专注于设计与结构搭建。可随着主梁逐渐升起,一个问题也摆到了眼前:
他们缺大木头。
不是普通的建材,而是可以撑起三层横梁的整根直木。镇上卖的木料要么太短,要么太细。有人建议用拼接结构,但卜丢摇了摇头。
“这是我们住的地方。房要靠得住。”
于是,他们决定再往森林深处走一趟,寻找传说中的直背杉和老榉木。
那天清晨,卜丢背着工具包,带着小白、灰兔、鼬獾,顺着旧河道向东而行,进入森林从未涉足的区域。草比人高,树缝里光影斑驳,一路上偶有飞鸟冲出,也有野蘑菇安静躲在树根下。
他们翻过两道小坡,绕过一片湿地,在一处山脚下发现了几棵沉稳粗大的老木树干。卜丢在树旁蹲下,用笔记在树皮上画了一道弯弯的记号,表示“预留”,他们不打算砍,只打算等秋天落木时收集自然倒下的那几根。
忙完后,大家都有些疲惫。
卜丢把布铺在林下的一块平石上,四周是野花盛开、风吹草动。他靠着树坐下,小白伏在脚边,灰兔躺在阳光斑驳的草地上翻肚皮,鼬獾找了块树影独自睡了过去。
整座森林像进入了梦的呼吸节奏中——阳光轻轻摇,风带着松脂的味道,连虫鸣都缓了半拍。
不知过了多久,一阵极轻微的花草窸窣声传来。
卜丢睁开眼时,第一眼看到的,不是树,不是风——而是一头小狮子,正低着头嗅着他旁边一簇淡紫色的野花。
它全身金黄,毛茸茸的脑袋带着自然卷,耳朵小巧,爪子略大还带点笨拙感,看起来像是刚断奶不久。它并不害怕,也不叫,只是缓缓走来,在花丛中嗅一朵又嗅一朵,尾巴甩得缓慢而优雅。
灰兔先醒来,站起身盯着它;小白抬头看了看,轻轻哼了一声,没吭气;鼬獾爬出树荫,一眼看到狮子,愣住三秒,然后竟然咕哝了一下,躲回了背后的袋子堆。
卜丢没有惊动那小狮子,只是低声道:
“你是哪来的?”
小狮子没理他,继续嗅完最后一朵花,然后慢悠悠地转身,走到卜丢脚边,盘腿坐下。
就像是走累了,需要歇会儿。
那天傍晚,他们一起回到了农场。
小狮子跟着他们一路穿过树林,穿过菜地,走进门槛,在灰兔旁坐下,小白绕着它闻了一圈,然后自觉给它让出水盆。
鼬獾远远看了一眼,又躲进灶台下面。
“它不是闯进来的,”卜丢说,“它是在花里长出来的。”
他们给它取名叫——花花。
从那天起,农场多了一道金色的身影,喜欢闻花、晒太阳,也喜欢靠在小白身边打盹。夜里它有时会发出像猫一样的呼噜声,梦里爪子轻轻动着,仿佛仍在闻那一朵从未记住名字的野花。